浆水菜,也叫酸菜
信息发布者: 盖文峰
盖文峰 2016-11-28 16:57:48 转载
题记:近日,咱们版块的网友侯海胜贴了一篇他写的文章《难忘妈妈做的"浆水菜"不烂汤》,写的很好,我就传在我的微信朋友圈。我的一位在骑兵第五师一起当兵的战友看见了,他是老北京人,虽然在三环里住着200多平米的豪宅,但对晋城人来说就是一土老冒,他回言说:“从未吃过,也未听说过,是雪里蕻吗?”我说:“你高高在上,光说浆水菜就是一门学问啊,多会讲给你听,和天书样。”朋友说:“不光我没听说,估计北京人百分之九十九的都没有听说过。”我说:“一会我给你发篇做浆水菜的文章,你瞜瞜。”于是,我把在冯匠写村志时写的一篇文章贴在这里让这位北京人看看。(这篇文章因为稍长,故在《冯匠村志》里没有用上,正好展示在这里)。
做浆水菜
浆水菜,也叫酸菜,是晋城乡民传统的佐餐配吃,也就是饭菜中的“菜”。在漫长的生产力水平不发达的社会里,它是村民的当家菜,可以说是一顿也须臾不可离,否则就是吃“甜饭”、“淡饭”。
以城边冯匠村为例。秋天,本地产的上青细下白粗,像个猪头一样难看的白萝卜成熟了,这时家家户户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用它做浆水菜。在集体化时期,土地统归大队种植,大队在东阁外划拨出几亩上好的水浇地做为菜地,叫“园地”,派有专人负责管理,每个小队抽出一个劳力。他们主要是栽种一些时令蔬菜,如豆角、青菜,而做浆水菜用的白萝卜,是由各个生产队来种,“头伏萝卜末伏菜”,每年小队在收罢麦子后都要专门留出一步分地来种萝卜。萝卜按人头分配,一般每人要分在150斤左右。那时的家庭人口多在六七口人之间,这样每个家庭可以分一千斤上下的萝卜。除了预留一点吃鲜以外,其余的统统做成浆水菜。
做浆水菜如同生产队收秋打夏一样,是个繁重而热闹的生活。因为这近千斤的萝卜必须一次制作完成,做好的浆水菜有几大缸,一般要做五缸。五个缸不一般大,中等的叫“四担缸”,可以放四担水;比它大的叫“老缸”,可以放比四担更多的水;小的叫“七斗缸”。老缸做两缸,四担缸做两缸,七斗缸做一缸。吃时是从小、中、大缸的顺序吃起。
一次做这么多,最好有邻居帮忙。好在那会儿村民住的是大杂院,四合院、八卦院中挤满了各家各户,不缺人。大家就采取互助组的办法,组织起五六个人,今天几个人帮你家,明天还是这几个人帮他家,直到各家都做完。这几个人中只有一个男劳力,之所以有一个男的,并不是像今天想像的那样“男女搭配,干活不累”,而是做浆水菜中的一个环节“捣缸”是件需要有强爆发力的体力活,非男子而浆水菜捣不成。
做浆水菜首先是淘洗。在院中备老缸一个,注满水,然后于其中把萝卜洗干净。千斤的萝卜挨着个的洗,一次把一推萝卜放进缸中,然后用火柱扎着一个萝卜在水缸中“圪咚”,也就是搅动清洗。圪咚洗干净了,就把它们放在院内的一层豆秸上控干滴水,再置于若干个大“花箢篓”,也就是好似大大的扁扁的无口篓筐中,或是置于铺在院里的席子上晾干。
除了洗萝卜以外,还要洗“黑菜”,就是萝卜缨,因为腌成后的萝卜是白的,这萝卜缨是黑的,故称。黑菜是浆水菜的重要组成部分,占约浆水菜原料的一半甚至一半以上,所以也得洗净。为了准备足够的萝卜缨子,在队里分萝卜带的缨子不够用时,社员还得到处找寻,如到西关、西吕匠等产萝卜较多却使用缨子少的地方去索要、捡拾。如还不够,就把别人掉在地中不要的白菜叶、白菜帮子也拾回来,洗净了充抵萝卜缨用。洗干净的萝卜缨不是摊起来晾干,而是要先过热水。
此时院中要专门盘炭火,敦上直径米许的“大斤锅”。水烧沸以后将洗净的萝卜缨子放入水中加热,“咧”(音:liē)一下,就是普通话里的“汆”,只不过时间很短就捞出来。这样操作后的萝卜和缨子容易发酵。咧过后将它们高高摞起来约有几十公分,上面放上荆条编的“篦子”,人或重物在上面使劲压,将多余的水分挤压出来,然后备用。
对洗净晾干的萝卜和咧过压干的萝卜缨要进行加工。萝卜是用专门的“挠”,也叫篣(音:páng)床,就是大号的挠。几个人“哧啦、哧啦”地得用一天时间来篣。萝卜缨,也就是黑菜的加工,也用专门工具切碎,刀叫“切菜刀”,形如战国时齐国的刀币,前段为刀背刀刃,后段为长长的刀把。下置“刀架”或“刀敦”,将萝卜缨握成束,推入刀架内,边推边切,越碎越好。
加工好的萝卜和缨子还要进行搅拌混合,让“黑”、“白”相间,便于更好的发酵和食用。之后是将搅拌好的黑白原料一层一层铺在缸内。
这时用到了男人,他双手紧握一个“捣菜圪垛”,也就是一个圆木棍前安一个专门雕圆的砂石工具可劲捣放入缸里的萝卜及缨子,目的是将它们捣瓷实了,犹如建房夯地基一样。每铺一层他就捣一层,直至萝卜及缨子堆到缸沿口。
其中每缸捣到大半截时,要在中间放两个整萝卜,其一长,其一圆,将它们包围在加工过的萝卜和缨子当中。来年吃的时候,再单独“挠”它们,做成卤面,叫做吃浆水菜卤面。
捣满了缸,在上面铺一层没有加工过的整缨子,缨子上再放一个篦子,最后在它们上面压一个牛头大的椭圆砂石,这一缸浆水菜算是做成了。
刚做好的成缸的浆水菜,为了让它们“酸”起来和长时间保存,有两种办法。一是用土封口。选用干净的黄土或红土,不加水和,直接堆一堆在缸顶,以后或湿或干均不管。只待需要食用时,取走土,挖去浮头的整缨子即可。另一种常用的办法是加些凉水。三天后和缸里萝卜的水一起“潮”起来,及时“押”了,就是“撇”(音: piē)了,将浆水菜上的水舀走,然后在加入新的清水。由于不断地浸泡、挥发,有时水浑浊了、干涸了,就需要及时的补充和换水,做到水不清就换,以保证浆水菜的新鲜。这项生活一直要坚持到最后一缸菜打开食用,时间长达几个月。小缸菜有半个来月就发酵味算可以食用了。
之所以说浆水菜是晋城村民的当家菜,一是食用时间长,二是一天三顿饭离不了,食用广泛。时间上从深秋开始吃,不仅要吃到来年开春犁地,还要吃到入夏收麦,更有的吃到和来年秋天新做的浆水菜接了起来。食用广泛是说顿顿里不开它,或用电油呼出一下当配吃,成为就饭吃的菜,或是直接放到米淇、汤面中当饭食。同时它担当着“填锅”的重任,一锅稀汤饭,舀它一大碗或者一小盆过来,投进去,立马这锅饭就感觉稠乎乎的。这对于干重体力活,需要吃干的劳动者来说,在视觉上是一个很好的安慰,虽然只是加了一点浆水菜,也就是一点萝卜和萝卜缨。当然,浆水菜也可以是纯干饭的组成部分,如吃浆水菜卤面,这浆水菜就成了实实在在的干货。
浆水菜之所以在村民的饮食生活中如此重要,是因为它原料丰富,制作简单,易于储存,便于搭配,吃起来也是酸香可口,清脆有个圪喳头,如果配以豆腐、豆芽,用油烘来一呼出,更是芬芳四溢,成为佐餐佳品。当然,在物质十分匮乏的年代,实际上人们也没有更多的菜肴供人选择,只有浆水菜独挑大梁,长时间称霸一方,养育着代代村民,伴随清贫走过了一段段壮烈的悲欢交加的日子。
浆水菜淡出村民的“缸碗”,这缸碗也就是一碗能放二斤粮食的粗瓷碗,一顿一碗就够一个劳力吃了的大白碗,时间是在土地下放以后。粮食多了是一个方面,主要是村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搞起了副业有了钱。有粮有钱谁也会吃,单一的缺乏营养的浆水菜很快就满足不了人们的需要,新鲜的时令蔬菜,高档的肉蛋奶油不断丰富着村民的餐桌,加上新兴媒体大肆宣传少吃腌制食品,以及住宅条件的变化,家庭人口的减少,浆水菜逐渐成为村民饮食中的配角偏房,以至于消失成为传说中的故事。
毕竟浆水菜给老一辈人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印象,至今有的人还会做一小菜缸浆水菜,没有做的,也会在小贩“浆水菜……豆腐”叫卖声中花2元买上一小袋现成的浆水菜,他们以这样的方式尝鲜、怀旧。年轻人偶尔吃上一顿浆水菜扯面,在用调和油把豆腐、黄豆芽和浆水菜烧成的浆水菜中,体验到了几许酸香、几许清脆。于是,他们会说:“嗯,还可以。”他们全然没有品尝到饱含在历史中的滋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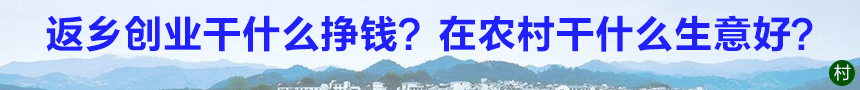
点赞
0
!我要举报这篇文章
相关热词搜索:
声明
本文由村网通注册会员上传并发布,村网通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村网通立场。本文如涉及侵权请及时联系我们,我们将在24小时内予以删除!




